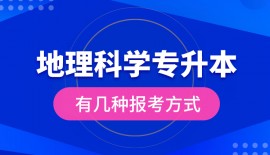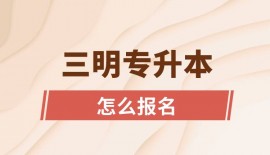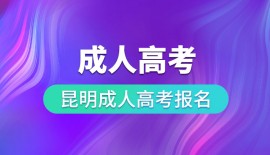感谢您关注“永大英语”!《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学风批评——《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后(上)张思武摘要:《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充斥着学理谬误、逻辑错乱、概念模糊、术语混淆,不去说明什么是或什么不是“真实任务”,反而玩弄假问题,谈空话大话废话。
事实上所谓的“真实任务”本身及其所衍生的“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等等都是伪命题。
对于任务型语言教学/语言学习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任务的“真实与否”,而是任务的“有效与否”——这才是外语教学研究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应该真正关注的。
因为,在任务型语言教学/学习中,任务是用来创造语言学习发生的环境和条件的手段,“手段”不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
关键词:任务型语言教学;真实任务;外语教学;二语习得近年来,在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小学英语骨干教师为主体的英语学科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和答辩中,笔者发现《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以下简称《真实任务》)对中小学英语教师、对基础英语新课改有较大的思想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对于基础英语新课改究竟是“福音”还是“祸害”,还值得从“学风”和“学术规范”两个方面探讨。
因此引出“四题之后”。
“四题之后”相关术语皆从“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①,不另说明。
个人的学风值得探讨,因其并非仅仅关系个人问题,更因其绝非我国学界的个别问题。
个人学风不正,不仅自己很容易滑到学术不端(关于《真实任务》的学术不端,笔者拟另文讨论②),还可能对后学构成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拥有“专家”“权威”头衔靠各种名义的基金项目养着的“著书立说”者,如其学风不正,对后学会更具欺骗性、危害性。
倘若学人对此现象熟视无睹,则团体的学风日下,最终使得学人引以为骄傲的“学术界”本身成为一种反讽。
笔者认为可以从道德层面和技术层面考察学风。
“学术的基本原则(追寻真理或客观性) 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张传文,2010),“追寻真理或客观性”要求做学问的人用纳税人的钱所研究的应该是真问题,要求做学问的人不能为一己之目的掩盖研究真相,不能以伪命题或学理谬误欺骗社会浪费资源误导后学。
“追寻真理或客观性”还要求做学问的人逻辑严谨、概念清晰、术语准确、有理有据,不能逻辑错乱、概念模糊、术语混淆、蒙人唬人。
笔者拟从这两个方面批评《真实任务》的学风。
《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鲁子问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3年5月第一版(2008年9月重印),32开本145页,“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小学英语教育动态真实原则研究与实验’研究成果”。
《真实任务》的学风问题可以概括为“假、大、空”。
所谓“假”者,指《真实任务》玩弄假问题,其“真实任务”“真实学习任务”“真实运用任务”等等其实是冠以“真实”的伪命题;也指其充斥着荒谬的逻辑、错误的概念、含混的术语。
所谓“大”者,指《真实任务》拉起“国家教育部”项目的大旗,并没有用心对“真实任务”进行理论探讨或逻辑分析,并没有用心去论证“真实任务教学”中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却企图与产生于延安窑洞的那部哲学著作同名,企图“以[真实任务]来规范我国中小学英语课堂的任务教学”。
所谓“空”者,指《真实任务》并没有“论证”或“论说”其提出的问题,除了超量堆积形容词“真实”,除了大话、空话、废话外,所谓“真实原则”“真实任务”“真实任务教学”等等,空空如也。
《真实任务》第一章题为“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理论基础”,除了第一节“任务型外语教学理论概述”(其作伪集中在这一节),就是第二节“英语教育的真实原则”,并不见其关于“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理论基础”的文字。
既然文不对题,那么,除了第一节,“英语教育的真实原则”就应该是这一章的重点,却只占整个篇幅不到1/145。
这段文字足以代表《真实任务》的“空”,照录于下:英语教育的真实原则是指:英语教师应该把握英语教育的教育因素的真实内涵,特别是英语教育的真实目的、学习者的真实学习目的和动力、真实学习兴趣和真实学习困难等(如真实的英语学习机制—[鲁子问]),并应该依据真实的英语教育因素,运用语义真实、语境真实、语用真实的英语教学材料、教学过程、教学策略、教学方法和技巧、教育技术,给英语学习者输入真实的英语,以有利于提高英语教育的教育质量、教学效率和教学成绩(鲁子问,2003:16)。
《真实任务》的这种“空”贯穿全书。
体现这种“学风”的另一个典型是第二章中有关“真实任务教学”,同样是几乎一个分句一个形容词“真实”: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就是基于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的真实目的和真实环境、我国中小学生学习英语的真实学习机制等真实教育因素,符合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教学条件等真实教学因素的任务型的教学,是以培养学生真实的英语运用能力为目的的教学(鲁子问,2003:18)。
如果有人想步《真实任务》之后尘,自立门户,自命权威,只要仿照《真实任务》的“学风”,将这些文字(以及书中其它地方如关于“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的文字)中的形容词“真实”换成其他修饰语如“快乐”“精彩”“趣味”“非常”等等,就可以如法炮制自己的“XX任务教学实践论”了。
在第一节提到国外权威论述之后,《真实任务》应该在作为“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理论基础”这一章主要内容之一的第二节讨论他自己的“真实任务教学理论基础”。
鲁子问也是这么想的。
他说:“笔者(鲁子问,2001:19—28)提出的‘英语教育的真实原则’可以成为国外任务教学成果在中国本土化转化的一个理论基础。
(鲁子问,2003:16)”③可惜《真实任务》似乎不知道何为“理论基础”,何为“原则”;其第二节并非以“理论基础”为题,而题为“英语教育的真实原则”。
所谓“理论基础”(rationale),根据《新牛津英语词典》解释,是关于方针、路线、信念、信仰的成套理由或逻辑基础(rationale,1998)。
笔者在“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一”中,借用埃利斯(R.Ellis)总结的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评价标准”(Ellis,Rod,1995:77—83),认为“理论基础”应该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完整地解释与一种复杂现象“相关的已知的事实”,应该能够以为数不多的几种主要机理就可以“构成可辨认的逻辑关联”,应该能够提出一种或几种机理来说明一种复杂现象发生发展乃至结束的全过程的变化。
《真实任务》这段文字以及书中其它任何地方既没有提出由一种或几种主要机理构成的可以辨认的“真实任务教学”(以及所谓“本土化转化”)的逻辑关联,也没有提出以一 种或几种主要机理为基础形成的能够说明“真实任务教学”(以及所谓“本土化转化”)发生发展全过程变化的一些理论、假设、理由或逻辑基础。
《真实任务》没有提出理由来论证“为什么”,甚至很少通过定义来限定“是什么”,只是要求应该“怎么样”。
看来“原则”与“理论基础”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真实任务》这里被搞混淆了。
《真实任务》说,“[鲁子问]提出了‘真实任务’的概念,以此来规范我国中小学英语课堂的任务教学,来促进国外任务教学成果在我国中小学英语课堂的本土化转化”(2003:18)。
这也应该是其主要部分,却只占整个篇幅约2/145。
其实,应用语言学中与“真实”相关的许多话题并不新颖,早在30多年前的1970年代就成为应用语言学关于交际途径原理论述的焦点话题之一,它所针对的应该是对语言材料“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倾向。
既然任务可以用于规则型的交际语言教学,交际途径原理论述也会涉及任务的真实。
不过,当应用语言学权威之一的威多逊(H. G. Widdowson)在1990年指出“过去大约10年间[交际]这个术语被如此随便地议论,被如此自由地用来作为赞许的一般标志,以至于其描述价值已经荡然无存(1990:117)”之后,尤其是当以任务为学习手段的任务型语言教学在1990年代末盛行以来,语言材料的真实就不再是外语教学研究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焦点了。
国外应用语言学关于任务途径原理和任务型语言教学④理论的讨论中,虽然初期会有人因循思维惯性一度提及“真实任务”,但是随着心理语言学的语言学习研究相关理论、假设、机理或逻辑基础的发展和成熟,主流论述已经不再关注“真实任务”或“任务的真实性”,而聚焦于任务的“意义”和意义实现过程的“自然”。
因为,对于截然不同的语言教学/语言学习途径,应用语言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交际语言教学追求语言运用“具体语境”的“真实”,而任务型语言教学则顺应语言学习“普遍路径”的“自然”。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及任务型语言学习理论研究权威之一的斯基汉(Peter Skehan)1998年在总结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任务概念与任务定义”共5点,其中包括最接近所谓“真实任务”概念的“与具有可比性的真实生活活动有某种关系的活动”(Skehan,1998: 95),没有提 “真实任务”。
国内与《真实任务》同年出版的《任务型语言教学》中,龚亚夫、罗少茜将国外应用语言学关于任务的各种定义归纳成14组,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八点,其中包括最接近所谓“真实任务”概念的“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活动有某些相似之处”(龚亚夫、罗少茜,2003:46—57),并没有将“真实”作为“任务”的限定。
关于“真实原则”“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的讨论只占整个篇幅的 3/145,而所谓的“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并无“论说”只见“描述”。
《真实任务》并没有解释什么是或什么不是“英语教育的教育因素的真实内涵”,什么是或什么不是“真实的英语教育因素”,实际上也就没有解释什么是或什么不是“英语教育的真实原则”。
《真实任务》超量堆积形容词“真实”,形容词后面就是空话、废话、套话,言之无物,让人无从着手批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真实任务》想对“真实任务教学”稍微说道的时候,例如在第二章“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就漏洞百出。
《真实任务》第二章声称提出了“真实任务”概念,并表示了想以“真实任务”概念来“规范我国中小学英语课堂的任务教学”的愿望,却没有定义什么是“真实任务”,没有说明“真实任务”针对的是什么或定义什么是“非真实任务”,就直接进入“真实任务”的下一个逻辑层面,将“真实任务”分为两大类。
“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真实任务包括两大类: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鲁子问,2003:18)。
因此,要辨别“真实任务”命题的真伪也只能从“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着手。
《真实任务》将“真实任务”分为“学习”与“运用”两大类,一开始就犯了学理错误。
自从海姆斯革命以来,应用语言学无论是关于语言教学如交际语言教学的论述还是关于语言学习如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论述,“学习”和“运用”都是不可截然划分的。
交际语言教学和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核心原理恰恰就是“学习”和“运用”的统一:弱势交际语言教学强调学习语言并学习语言运用即所谓“学并用”,强势交际语言教学强调运用语言而意在学习语言的运用规则即所谓“用而学”(Howatt,A.P.R,1984:286—87),以及任务型语言教学通过任务实施意义实现即语言运用的语言学习过程,都是“学习”和“运用”的统一。
换句话说,任务型语言教学中的“学习任务”就是“语言运用”。
第二章“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讨论的是中小学英语教学,无论是根据交际途径原理还是根据任务途径原理,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的区别。
《真实任务》坚持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交际途径发展论”,却在“学习”和“运用”区分上背离交际途径原理和任务途径原理,暴露出应用语言学原理方面的破绽。
关于“真实学习任务”,《真实任务》说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知识学习活动”,并试图从反面说明什么是“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的真实目的”(或试图从正面说明什么是 “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知识学习活动”):我们知道,中小学生在运用英语时并不需要掌握英语的所有知识、技能等,比如字母发展历史的知识、南非白人英语与南非黑人英语的异同的全部知识、辨别东伦敦与西伦敦的口语特征的听力技能、阅读中世纪英语文献的阅读技能、布道的口头表达技能与文化情感等,这些都不是我国中小学生需要的知识、技能、文化、情感等。
那么,真实学习任务就必须以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的真实目的为依据(鲁子问,2003:19)。
《真实任务》是否知道,不单中小学生在“运用英语时”不需要掌握英语的“所有知识与技能”,任何人—不仅是学习英语的学生—在“运用英语时”都不需要掌握英语的“所有知识与技能”, 任何人—不仅是学习语言的学生—在运用语言时都不需要掌握语言的“所有知识与技能”。
《真实任务》是否知道,这些反面例证纯属假问题。
《真实任务》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这些问题,不单中小学英语教学不会考虑,大学英语专业本科教学也不会考虑,英语硕士研究生英语博士研究生如果(学位论文)不以此为研究对象也不会考虑。
如果真不知道,那么《真实任务》在提出“真实任务”概念和“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之前似乎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如果假不知道,那么《真实任务》就有以假问题糊弄“国家教育部”骗取项目基金之嫌。
这些反面例证因为是假问题,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什么是“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的真实目的”。
《真实任务》并没有说明什么是“真实学习任务”必须引以为依据的“真实目的”。
相对于《真实任务》从正面说到“真实学习任务”时,只是说它“必须是指向英语运用能力的学习活动”(堆积形容词“真实”的话语除外),《真实任务》从正面说到“真实运用任务”时,提出了“真实的生活”或“指向真实生活”“运用英语”是否“此时此刻”发生和运用英语的“真实目的”:真实运用任务显然就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运用英语,不过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英语国家,英语也不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生活语言,因此,我们有很多运用任务只是指向真实生活,并不都是完全的真实生活(鲁子问,2003:19)。
《真实任务》告诉读者,“我们有很多运用任务只是指向真实生活,并不都是完全的真实生活”。
那么,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究竟有没有或究竟什么是《真实任务》所谓的“在真实的生活中运用英语”的“真实运用任务”呢?这一点至关重要,是《真实任务》将“真实任务”区分为“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的根据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真实任务》避而不谈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如同其在前面回避“真实任务”一样。
“完全的真实生活”和“真实生活”是种属关系,“完全的真实生活”属于“真实生活”。
《真实任务》既说指向后者,又说指向非前者,岂不矛盾?按照《真实任务》的逻辑,“真实运用任务显然就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运用英语”,而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是否是“真实的生活”或“完全的真实生活”,就看那个国家是否是英语国家或英语是否是其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生活语言。
这是什么逻辑?斯基汉在讨论任务定义时,说任务是“与具有可比性的真实生活活动有某种关系的活动”,将任务型语言“教学活动”与“真实生活活动”区别开来。
而《真实任务》则将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课堂活动”与“真实生活”混为一谈。
笔者猜想,《真实任务》或许是想区分二语与外语,因为书中多次提到国外任务型语言教学成果“本土化”,而根据 “语言环境(language environment)”区分习得与学习、二语与外语等等是一切“本土化”或“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的议论的出发点(参见《外语教育教学基本理念辩论》(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编辑部,2007))。
如果是这样,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语言活动(语言教学或语言学习)发生的环境是目的语环境还是非目的语环境”,而不是“真实的生活”“指向真实生活”或不完全的“真实生活”,虽然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主流研究并不区分学习发生的语言环境以及习得与学习、二语与外语等等(Ellis,Rod,1985:8;Ellis,Rod,1997:3)。
归根结底,不能够用学习发生的语言环境来划分出所谓“真实生活”。
紧接着,《真实任务》提出“运用英语”或“真实生活”是否“此时此刻”的问题,以此来区分两种“真实运用任务”,其中“指向真实生活的活动中”的“运用英语”不在“此时此刻”发生,区别于“真实生活中”的“运用英语”:我们的学生在真实生活要识别颜色,并用英语告诉讲英语的人这些颜色,这是中国中小学生的真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但可能不是此时此刻。
因此,我们让学生在此时此刻用英语识别颜色的任务不一定在此时此刻是真实的,但却毫无疑问是指向真实生活的(鲁子问,2003:19)。
首先必须指出,该任务(学生识别颜色并用英语告诉讲英语的人这些颜色)既然“可能不是”此时此刻(发生),那也就意味着“可能是”此时此刻(发生)。
《真实任务》以任务“可能不是此时此刻”为唯一可能,不顾其“可能不是”应含的 “可能是”,其“因此”的结论不能成立。
“我们让学生在此时此刻用英语识别颜色”,就说明该任务“此时此刻”发生了。
“此时此刻”的该任务怎么会“并不一定在此时此刻是真实的”呢?《真实任务》没有告诉读者怎么会是这样的理由,只是告诉读者,该任务“可能不是此时此刻”发生,然后该任务“此时此刻”发生了,“因此”该任务在此时此刻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这是什么逻辑?此时此刻实施的任务怎么就变成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了?是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课堂活动中用英语识别颜色不真实吗?是课堂活动中出现“讲英语的人”不真实吗?是课堂活动中“用英语告诉讲英语的人这些颜色”不真实吗?笔者认为,如果“真实”是值得关注的真话题,在课堂活动中“用英语告诉讲英语的人这些颜色”其实是真实的(“讲英语的人”可以是以英语为母语者,也可以是实施该任务的学生的同学或老师);相反,在真实生活中(非课堂教学活动中)“用英语告诉讲英语的人这些颜色”可能是非真实的——如果“讲英语的人”是以英语为母语者。
《真实任务》再次将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课堂活动”与“真实生活”混为一谈,因而逻辑混乱。
《真实任务》在此处不但暴露了混乱的逻辑,也暴露了谬误的学理。
《真实任务》中谈论的“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都是“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真实任务”,其中的 “运用英语”就必定是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任务实施(即语言运用)教学活动。
按照《真实任务》的解释,在中小学任务型语言教学活动中,有的任务实施“即时发生”,有的任务实施“延时发生”。
这就违背了任务途径原理。
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运用语言实施任务解决问题来学习语言。
任务型大纲是以非语言内容设计的手段大纲,其教学活动是“非规则型”(non-rule-based)的“任务型”(task-based)的;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以语言内容设计的目的大纲[12]193,如传统语言教学大纲和交际语言教学大纲,其教学活动是“规则型”(rulebased)的,其教学活动的内容就是其教学目的。
目的大纲的语言活动能否或何时实现其教学目的也许可以成为语言教学研究的一个话题,但是手段大纲的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语言活动不是目的,而是用来创造语言学习发生的环境和条件的教学手段。
在以语言运用任务实施意义实现为手段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手段采用”(即任务实施)是“此时此刻”发生的,不存在“手段采用”(即任务实 施)“延时发生”问题。
如果在当前的语言教学活动中观察不到作为手段的任务实施即语言运用,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当前正在进行的语言教学活动不是任务型的。
换句话说,如果“学生在此时此刻用英语识别颜色的任务并不一定在此时此刻是真实的”成立,那么所谓的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在真实的生活中运用英语”的“真实运用任务”就不存在。
《真实任务》在提出两种不同的“真实运用任务”时,还提到了“真实运用任务”的“真实目的”,说“真实运用任务”是在“真实生活中”或“指向真实生活的活动中”为了“真实目的”而运用英语的“生活活动”(鲁子问,2003:18)。
与其试图以反面例证来说明什么是“真实学习任务”必须引以为依据的“真实目的”不同,《真实任务》在后面的文字中不再提“真实目的”,而提“语用目的”:判断真实运用任务的真实性,必须考察的是:任务是否是语言本身的语用目的,在中国中小学生运用英语的真实语境中这些任务是否可能,在实施任务时语义表达是否真实(鲁子问,2003:19)。
什么是“语用目的”?什么又是“语言本身的语用目的”?《真实任务》只是虚晃一枪,并没有说明或解释。
所谓“语用”,就是语言运用,就是“doing things with words”(Austin,J. L.,1962)。
人们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Widdowson,H. G.,1996:130)或“语言环境以及非语言环境”(Cook,G.,1998:249)使用语言时“用意何在”,应该是“言者”的目的,而不是“语言本身”的目的。
根据交际途径原理,一个表达或命题本身(“语言本身”)只有字面意义或命题意义;只是在语言运用时,由于语境的作用或制约,一个表达或命题才可以有好几个“交际功能”表达好几种“交际意义”,而不同的表达或命题也才可以有相同或相似的“交际功能”和“交际意义”(张思武,1990)。
但是说到“用意何在”,则是指运用语言的人在语言运用时希望通过语言达到的“目的”。
如果“语言本身的语用目的”命题成立,那么社会语言学革命(及其产生的交际途径原理)所强调的语言运用的“社会语言环境(sociolinguistic context)”以及与社会语境紧密相关的“真实”话题就没有多少重要性了。
关于语用的这些概念,《真实任务》似乎并不清楚,只好虚晃一枪,但是“语言本身的语用目的”还是暴露了其应用语言学学理方面的无知和“假、大、空”的学风。
更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任务型语言教学(以及其他非规则型语言教学)与规则型语言教学(如交际语言教学)不同,“任务”只是教学手段,不是教学目的。
采用何种教学手段即任务,需要考虑的主要是任务作为手段的“有效性”,即任务本身能否或是否有利于创造语言学习发生的环境和条件。
因而,对于任务必须考察的是“任务的两个根本特征,避免特定的结构,以及从事值得的意义”(Skehan,P.,1998:96),而决不是所谓的“语言本身的语用目的”。
这是因为,一方面,“避免特定的结构”是为了追求语言学习的自然性属性,而实际上避免了由语言规则或语言运用规则来决定语言学习的内容和顺序;另一方面,“从事值得的意义”是因为并非所有的任务实施意义实现都是“值得的”,都具有应用语言学价值(张思武,2007)。
此外,关于“真实运用任务”,《真实任务》在此处还提出任务在真实语境中“是否可能”,语义表达“是否真实”。
自从海姆斯革命把相对于形式的“意义”纳入语言学研究,“是否可能”在应用语言学论述中就指语言形式的“可能性”,即语法是否正确,与语境或真实语境基本上没有关系。
《真实任务》这里的“是否可能”以及“是否真实”,根据其限定的“真实语境”判断,应该是指语言意义(任务实施语言运用)的“可行性”“得体性”和“可接受性”(Hymes,Dell,1979: 19)。
《真实任务》处处坚持任务型语言教学的“交际途径发展论”,却对交际途径原理关于“可能性”以及“可行性”“得体性”“可接受性”的这些基本术语不甚了了,含混不清。
澄清了关于“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的上述谬误之后,《真实任务》第二章关于两种“真实任务”的说法就剩下“学习活动”与“生活活动”的区别了。
《真实任务》说 “真实学习任务”是“基于中小学英语教育的[……]教学活动”,“是指向英语运用能力的学习活动”,而“真实运用任务”是“在真实生活”中或“指向真实生活的活动”中“为了真实的目的而运用英语的生活活动”(鲁子问,2003:18-19)。
《真实任务》在第二章议论的是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所谓的两种“真实任务”—接下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进一步涉及“中小学英语真实学习任务教学”和“中小学英语真实运用任务教学”,但是第二章并没有说明什么是“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真实任务”的“学习活动”与“生活活动”,没有论证“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真实任务”中存在着“学习活动”与“生活活动”的区别,也没有或不能论证“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真实任务”中存在着区别于“教学活动”的“真实生活”。
如果顺着《真实任务》的“思路”,“真实运用任务”的“指向真实生活的活动中”的“运用英语的生活活动”,应该与“真实学习任务”的“指向英语运用能力的学习活动”一样—按照《真实任务》的解释—都指向“延时”的任务实施即将来会在真实生活中实现的意义;而“真实运用任务”的“在真实生活中”的“运用英语的生活活动”,应该与“真实 学习任务”的“指向英语运用能力的学习活动”一样—按照《真实任务》的解释—都是“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真实任务”语言活动。
既然都与“真实学习任务”的“指向英语运用能力的学习活动”一样,所谓的“学习活动”与“生活活动”区别就不存在,所谓的“真实学习任务”与“真实运用任务”区别也不存在。
再者,换一个角度来看,既然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课堂活动中不可能存在“即时发生”与“延时发生”区别,因此,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并不存在“学习活动”与“生活活动”区别,因而也不存在“真实学习任务”与“真实运用任务”区别。
《真实任务》这些所谓的区别,都是因其混淆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课堂活动”与学习者的“真实生活”而产生的逻辑错乱。
既然《真实任务》不能证明“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存在“学习活动”与“生活活动”区别,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真实任务”就是“真实生活”?“中小学英 语教学中的真实任务”就是“真实生活”的“生活活动”?其 “学习活动”就是“生活活动”?反之亦然,其“生活活动”就是“学习活动”?如果不能说明什么是“学习活动”和“生活活动”区别,那么,怎么判断什么“学习活动”不是“生活活动”?怎么判断什么是“真实任务”或什么不是“真实任务”?如果 不能证明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真实任务与非真实任务的 区别,那么,“真实任务”概念意义何在?笔者认为,语言教学/语言学习理论和实践中,所谓“真实任务”既无法从范畴上来识别判断,亦很难通过量化从程度上来识别判断;同时,任务的真实与否还取决于参照系,因参照系相对而言。
学习者的学习生活就是他们完成学业以前的真实(实际)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学习生活为参照系的教学活动都是“真实”或“真实任务”;而参照学习者完成学业以后的社会活动(包括工作生活),无论逼真到什么程度的任务(教学手段)都具有非真实的成分,这就是逼真的教学活动通过任务(教学手段)想要实现的、与真实(实际)生活目的不同的教学目的,以及为实现此教学目的而对任务(教学手段)的设计、改编、实施、操控、评估。
《真实任务》关于“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真实任务”的“学习活动”与“生活活动”的无理区分反倒告诉读者,中小学英语任务型教学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真实学习任务”与“真实运用任务”的区别,任务型语言教学中的“任务”应该无所谓真实与非真实。
任务型语言教学中并不存在非真实任务,又何谓“真实任务”?对于外语教学研究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任务的“真实与否”,而是任务的“有效与否”——这才是语言教学研究与语言学习研究应该关注的真问题。
因为,在任务型语言教学中,任务是用来创造语言学习发生的环境和条件的教学手段,“手段”不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
任务型语言教学研究与实践(包括任务的设计与实施等等)考虑的问题是“避免特定的结构”和“从事值得的意义”,因为,作为教学手段,任务的“有效性”体现在任务实施“不导向一致”从而保持任务型语言教学/学习的自然性属性,并且意义实现具有应用语言学价值——促使学习者的中间语系统朝向目的语发展(张思武,1990)。
《真实任务》没有论证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学习活动”与“生活活动”的区别,不能论证“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的区别,关于“真实任务教学”则是堆积形容词的废话套话空话,避而不谈关键问题什么是或什么不是“真实任务”。
《真实任务》并没有说明什么是“真实任务”,更不用提什么是“真实任务”的应用语言学逻辑基础和逻辑关联,也没有说明构成“真实任务教学”“真实学习任务教学”与“真实运用任务教学”的成套理由的应用语言学理论、假设、原理和机理。
总之,《真实任务》的这些区别既没有逻辑,又违反学理。
《真实任务》的逻辑错乱、概念模糊、术语混淆的学风在第二章这两页文字暴露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真实任务》不能说明什么是或什么不是“真实任务”,“真实任务”及其所衍生的“真实学习任务”和“真实运用任务”等等都是伪命题。
所谓的《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充其量不过是以“本土化”为幌子改编的任务型语言活动的操作手册(manual)。
这样学理谬误、逻辑错乱、概念模糊、术语混淆的“国家教育部”项目“研究成果”最终只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贻笑大方。
笔者“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实乃因《真实任务》的“学风”和“作伪”问题而发。
四题之后,言犹未尽。
遂作“四题之后”,以正视听。
注释:① 此“四题”分别是:张思武《论任务型语言学习的理论基础——〈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98-107页;张思武《国内任务型语言教学辕学习理论研究检讨—〈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59-67页;张思武,余海燕《论任务型语言学习与交际语言教学的本质区别——〈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三》《,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136-144页;张思武《意义与形式之间的复杂:均衡发展任务型指导原则 ——〈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四》,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82-91页。
②《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后》(初稿)完成于2008年夏,18千字,针对《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的学风和学术规范,因某学术期刊编辑认为篇幅太长,遂一分为二,上批评其“学风”,下检举其“作伪”。
③虽然鲁子问在《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中没有讨论何为“国外任务教学成果在中国本土化转化”,但是,从应用语言学的心理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伪命题。
相关理论请参阅笔者《论任务型语言学习的理论基础———〈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
迄今为止,未见可以说明外语教学“中国本土化”发生发展乃至结束的全过程变化的一种或几种机理或逻辑关联。
④本文不区分任务型语言教学和任务型语言学习。
对于二者的区别“四题之二”已专作详细讨论;为方便计,本文用任务型语言教学统称。
参考文献[1]Austin,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2]Cook,G. Pragmatics [A]. In K. Johnson & H. Johnson (Eds.)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C]. Oxford:Blackwell,1998.[3]Ellis,Rod. Apprais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in relation to language pedagogy [A]. In Guy Cook, Barbara Seidlhofer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4]Ellis,Rod.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5] Ellis,Ro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6]Howatt,A. P. R.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7] Hymes,Dell.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In C. J. Brum & K. Johnson (Ed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C].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8] Johnson,K. An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01 Pearson Edition)[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9]rationale.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K[) Z].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0]Skehan,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1]Widdowson,H. G.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2] Widdowson,H. G. Linguis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3]龚亚夫,罗少茜. 任务型语言教学(修订版)[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4]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编辑部. 外语教育教学基本理念辩论——我国学校外语课依靠自然性习得还是自觉性学得[J].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7.[15]鲁子问. 中小学英语真实任务教学实践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6]张传文. 林毓生、余英时论汪晖事件:清华大学应负起政治与道德责任 [N/OL]. 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10-06-06.[17]张思武. 英语基础阶段交际能力培养探讨[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18]张思武. 任务型语言学习的理论基础——《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一[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6).Criticism of the Study-style in On Practice of Real Task Teaching in Elementary/Secondary School EnglishZhang SiwuAbstract: Congested with fallacy in principle,chaos in logic,obscurity in conception and confusion in terms,On Practice of Real Task Teaching in Elementary /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Zhongxiaoxue Yingyu Zhenshi Renwu Jiaoxue Shijianlun) does not undertake to account for what is or what is not“real task”;instead,it plays with false issues and indulges in tall-talking,empty-talking and nonsense-talking. In fact,the so -called“real task”itself and“real learning task”and“real use task”derived from it are pseudo- propositions. For TBL language teaching / language learning there is whether a task is efficient or not,rather than whether it is real or not,which is there concern of TESOL or SAL research. For,in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 language learning,a task is a means employed to create context and conditions for language learning occurrence,where there is no true-or-false problem.Key words: TBL;real task;TESOL;SLA(本文首次发表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小学英语课堂教学实践研究(中小学英语教学研究与实践)
 百科信息网教育知识
百科信息网教育知识
- 上一篇: 幸福树的含义和寓意
- 下一篇:burberry是什么品牌的牌子
最新教育知识
浏览量(730)
2025-02-04
浏览量(105)
2025-02-04
浏览量(394)
2025-02-04
浏览量(446)
2025-02-04
浏览量(89)
2025-02-04
浏览量(716)
2025-02-04
热门推荐
为你推荐
浏览量(131)09:07:58
浏览量(80)16:35:07
浏览量(66)13:55:01
浏览量(82)13:53:43
浏览量(125)14:15:59
浏览量(103)13:15:58
浏览量(101)13:33:17